吕植专访 | 去经历世界的另一面
2019-12-14
 说在前面:
说在前面:

Q1:您曾在秦岭做了10多年的野生大熊猫研究,是什么机缘带领团队来到三江源做研究和保护?

 社区会议
社区会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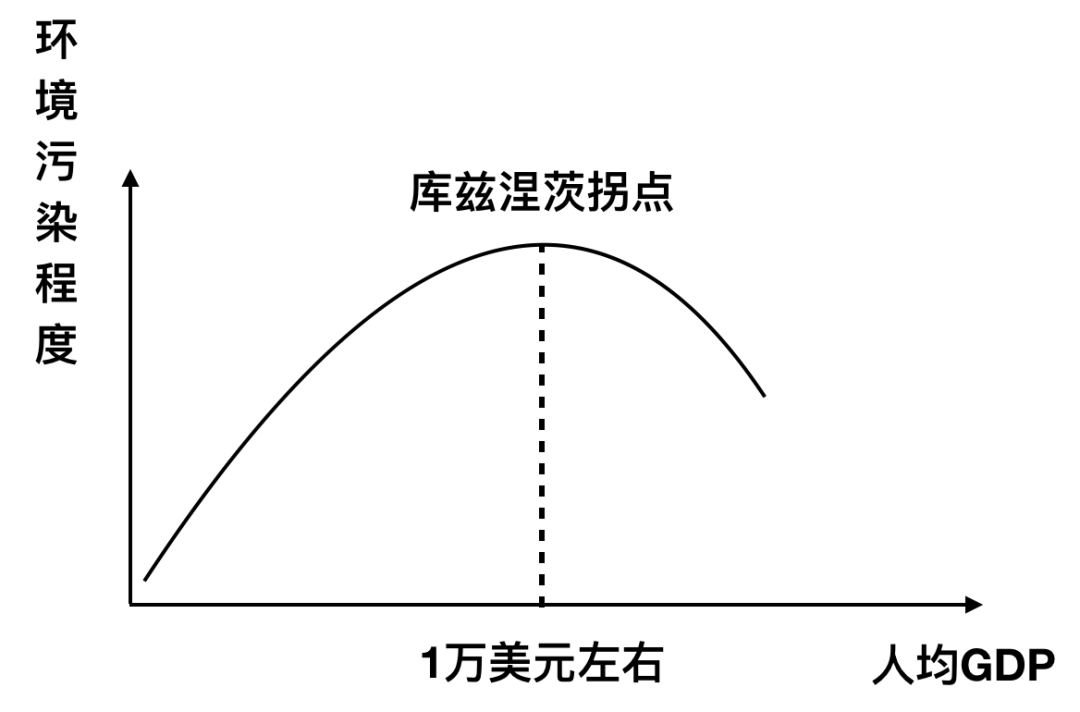
Q2:提到您北大教授的身份,我们总是想到教学、科研、申请项目这些规定动作。是什么促使您创办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推动生态保护?
 2019届山水研修生关坝社区培训
2019届山水研修生关坝社区培训Q3: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模式在三江源成果丰硕,还存在哪些挑战?
 在自然保护复杂的表征背后,是解决野生动 物和人类尤其是原住民共存的问题。
在自然保护复杂的表征背后,是解决野生动 物和人类尤其是原住民共存的问题。Q4:三江源保护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山水如何应对?

草原治理与生计发展研讨会上,NGO、政府、研究人员和牧民通过参与式讨论的方式一起聊草原。
Q5:关于月捐人项目,自然观察节搭建了保护地与外界沟通的平台,公众参与的热情很高,带来了哪些变化?

Q6.我们与山水合作公民科学家行动,希望打开一扇窗,引导更多城市里的人真正参与生态研究和保护,您对此有什么期待?
 面向公众的自然观察活动
面向公众的自然观察活动Q7.山水一直倡导生态公平,回到“益心华泰 一个长江项目”,从长江源到中下游,生态公平如何实现?

Q8.一代又一代人投身的自然保护事业,最理想的状态是怎样的?
 早年间,吕植与乔治夏勒博士、潘文石教授在秦岭地区的保护工作掠影。
早年间,吕植与乔治夏勒博士、潘文石教授在秦岭地区的保护工作掠影。Q9.关于未来,您理想中的山水,是怎样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