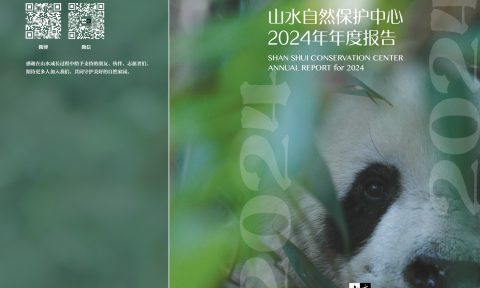志愿者手记 | 南仁萨勇:保存与转译之间
写在前面:
7月的南仁萨勇保护地,高山植物正迎来“丰盛”的花期。为了让更多朋友了解南仁、萨勇两个保有传统与历史的藏族村落,促进当地自然体验的发展,山水邀请志愿者们来这里做客,用各自新鲜的视角传递村子与自然的故事。文本的志愿者韩倩记录了地方的传统文化及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在人与自然、社会交织的整体中,她尝试用更广阔的理解力感知人与自然的处境。(后续还会有更多志愿者的文字与影像,带你看见这片土地的不同面貌~)
感谢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德钦县羊拉乡南仁社区、德钦县羊拉乡萨勇社区的协助,感谢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上海蚂蚁森林生态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公益支持。
“历史大潮浩浩荡荡,人类的命运也被洪流激烈的冲荡着。所有参与过这次滇金丝猴保护运动的人,命运也都被改变了,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
——肖林《守山》[1]
过去几年里,每年我会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云南。在滇西北这个地方,我是个外来者。当我穿梭在没有道路的丛林中寻找方向,在骤降气温的高山中努力保持体温,意外窥见熊在森林里留下的抓痕,向呼啸而来的牦牛匆匆让出道路,被草叶上成片的蚂蝗叮咬染红的裤腿,与密林里一只回眸即逝的毛冠鹿对视,一只雉鸡在山林雾气的半夜撞进怀中又惊飞,海拔快速爬升带来的无法抑制的喘息和心跳……那些或惊险或奇遇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曾经对自然的经验竟是如此单一。
我的徒步经验始于欧洲,那些和十七世纪西方风景画一样干净壮美的场景曾给过我极大的满足与慰藉。也正是在同一时期,欧洲社会型塑出自然与社会的二分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社会和自然几乎是被同时发现的。“自然”被当作一个被动的客体,可以被命名、描述、测量、再现;而“社会”则是一个能动的主体,是解释与赋值的来源。因此,那样“干净”“安全”的自然风景是自第四纪冰期结束之后、尤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被人类不断清除、隔离、驯化的结果。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加剧了这种破坏,伴随着人们对荒野的逐步排斥,共同塑造了我们今日所见的——被人类深度干预后的——生态系统,以及单一而受控的自然景观。一种可被欣赏、被利用、却难以真正进入的自然幻象。特别是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农耕生产后的今天,那种从未被更改过的土地和自然,仅仅存在于想象当中。
Parco Naturale Tre Cime,意大利
也正因欧洲的行走经验,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西南这片荒野和其背后文化的珍惜宝贵。只是,曾经人迹罕至,需要徒步很久才能到达的地方,如今在社交媒体上被赋予“生态秘境”等充满异域想象和噱头的字眼,在越野车的带领下,人们可以轻松降临。那些为了适应恶劣环境的高山植物,用千百万年进化出不同于低海拔地区的特征,曾经面对无垠的世界肆意绽放,如今却面临被踩踏和采摘的风险。生物多样性的危机不只是高山植物,那些本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被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占据,它们或逐渐退隐至中国最边缘的地区、或由此引发越来越频繁的人兽冲突事件;全球持续的高温、暴雨、洪灾、山火等极端气候激增所叠加的危机不断加深。

南仁村的布布带我们找到的总状绿绒蒿,高山花卉的代表绿绒蒿,在全世界有四十多种,而中国就有三十多种
面对整个生态系统所承受的持续性崩塌,除了无力与愤怒之外,如何在简单的立场和偏颇扁平的话语之外寻找到某种锚点或把手?如何具体地看到环境保护与地方、人之间动态的张力,以及那些与此相关更为复杂和立体的现实遭遇?我带着现实的种种疑问和无法回避的、一种需要身体力行的迫切选择,作为志愿者加入了山水在南仁萨勇保护地的工作。除了山水的四位工作者之外,我们一行六名志愿者都是女性,所处的年龄与行业各不相同,但大家因为对环保事业共同的热枕与关切聚集于此。
01 初见南仁萨勇:缠绕的生命网络
南仁和萨勇两座村子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从香格里拉开车前往还需要两三个小时。这里不仅是藏族的家园,同样也是滇金丝猴的栖息地。当车行驶至白马雪山保护区界牌时,我仿佛已经看到肖林穷尽一生去保护的山野和栖息其中的野生动物,特别是与他牵绊一生的滇金丝猴。
坐落于干热河谷的萨勇村,曾经叫做萨隆,是藏语百鸟谷的意思。一位与肖林同样痴迷于拍滇金丝猴的藏民安吾农布,他有着黝黑健壮的体格,对于不熟悉藏地只说汉话的外来者,他显得有点难以接近,但当我们攀谈起来,他腼腆的笑容和断断续续的汉话让人心生暖意。透过他这些年拍摄的影像,我们看到以家庭为单位的滇金丝猴跳跃在高山栎树之间,或寻找食物或嬉闹玩乐。我一边想着此行应该是见不到野外的滇金丝猴,一方面也暗暗庆幸这些毛孩子们仍保持着对人类的警戒心和距离。
虽然此行的初衷,是在山水的协调下,与两个村子的村民共同探讨:如何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的前提下,推动可持续生态旅游的可能性。但于我而言,更深的触动是,这里向我打开了另一片世界图景的窗口。曾经我与之共振、暗下决心一生都会为之努力的事物,以另一种极度生动、真切的经验与感知流动在这片土地和栖息于此的人之间。在这里,人们或许未曾接触关于生态、生物多样性的知识体系,却早已在日常中内化并延续着其中的行动逻辑。
出生在萨勇村的此称老师,是当地少有能读写藏文的人。在藏地,懂得藏文、医术以及能讲述世代相传故事的人,被视为藏族的知识分子。我后来发现,此称不仅是这一地区的知识分子,也是有名气的青年诗人。我们一行六名志愿者中有几位早就听闻过此称,读过他的诗和文章;我和此称也有着在艺术界和人文社科领域的好些共同友人。
此称带着我们去拜访他的藏文启蒙老师——鲁荣师傅。经历过前几日的热情款待,如预期一般地,九十多岁的鲁荣爷爷的客厅里也摆放着一桌子的零食饮料,随时迎接客人。在他娓娓的藏话和此称的翻译中,我很快就掉入进“白海螺”“巫师”“树神”“白岩秘境”这些远古的想象与秘径。对于不在这样叙事中成长的外来者,理解这些故事必然是困难的。但那些无法被转译、理解的部分恰恰是由无数记忆、神话与身体经验共同构成的、活着的地貌。
那些故事不是讲给我们听的,而是以一种更根本、更深远的方式,牵连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这些故事的流传中,存在的万物都被看成一种可以被理解的、感知甚至沟通的对象,它们的存在是有神山赋予其的职责。在这样的视阈中,与生物多样性暗藏缤纷的生命网络不谋而合,每个物种都在自己的生命周期中完成着外在于人又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命意义,这样的意义远远超出被人观看或利用的浅薄范畴。

萨勇村鲁荣师傅(左),当地作家、诗人此称(右)
因此,当地村民有着伐木的公约,盖房只能用倒木。但每当要伐木时,村民不仅要向当地林业部门申请砍伐指标,也需要煨桑求得山神的应允。藏族人的日常中,煨桑是不可或缺的仪式。不仅每个村子里有公共煨桑的地方,每家每户也都有各自煨桑的地方。萨勇村在赛坡煨桑时,雨中茫茫烟雾。马老师告诉我们,在藏族人的眼中,那些被风带到山脊之上的袅袅烟雾,是献给山神与诸灵的礼物。如果有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山神的惩治是会降临的。
除了山神的惩罚,活佛也深刻影响村民日常行为的伦理边界。在南仁村,我们住在布布家。他生动地描述山中土拨鼠如何以家庭为单位群居,分工协作、轮流放哨。过去,偶有外地人前来盗猎这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自从活佛明言不可再捕杀后,这种行为便迅速停止。
某日适逢村民休息,大家邀请我们参加集体烧烤。布布提到,那天烤的猪是从外面买来的,因为活佛说每个月有固定不得杀生的日子。这种在村庄内部共享的共识实践,在节制与敬畏中维系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太大和太老的菌子要留给山林自然腐化,太小的菌子还需要生长,只可以摘中等大小的且不可破坏菌丝网络
凭借着这样对生命和关系的感知、彼此牵引,他们拥有着在环保准则、法律道德之外的,对自然的理解与关照。在这里的每一个村庄都有祖辈确认流传下来的神山,每个村落的周围几乎都是大大小小的神山。神山是需要世代保护、按照自然的规律自生自长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中,一座连着一座的山脉都在关怀和庇佑下得以延续。
此称说过,藏族祈福时并非首先为自己祈求安康财富,而是在众生离苦等更宏大的祈愿之后,才会轻声许下关于自己的愿望。因为在他们的叙事中,人的存在是需要放在整个自然中去考量的。而在我通过盖娅、人类世和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中获得的知识与本能的感知,是传统世界中再日常不过的理解。我不禁嘲笑起自己,像是一个早已脱离自然在城市中游荡的无根幽灵。
02 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渗透
但在这样的智慧和愿景中,仍存在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博弈。我们此次住的地方是两个村子搬迁后的新村,虽然距离老村不远,但是老村的藏房和现在的截然不同。老村曾经使用的筑房材料是夯土墙和泥土充墙,每家每户都会互相帮衬共同完成,使得关系流动在每一次的日常和劳作之中。如今,新村使用现代的建筑材料,需要请外面的人来搭建房子。因此,无法像曾经的传统社区那样共同协作。新村的样貌象征着现代性的渗透——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空间的组织方式,也在悄然松动一个社区赖以维系的协作机制与价值认同。搬迁或许并非只是地理上的转移,它也意味着某种生活方式、语言、节奏与感知的替换与重组。

到达南仁村的第一晚,村里的公房
在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下,不同少数民族和传统文化正在迅速吸纳他者的语言。为适应游客对“异域”想象的期待,一个又一个的现代神话被建构出来——在游人如织的云南,许多原本并不食用的花草,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并不属于当地传统的“地方菜”。比如,在腾冲地区有一种特有的滇北球花报春,当地人发现其对游客的吸引,开发了一种被冠以传统菜肴之称的新菜“报春炒腊肉”。在极短的时间内,当地的报春被薅至绝迹。
在藏地,当地所面临的文化危机似乎更为深刻。一方面,年轻一代对藏语与藏文的使用日益稀薄;另一方面,成年人原有的生活方式与生计结构也正快速松动。我们到访时正值暑假,许多孩子和在外读书的大学生都回到了家中。与孩子们交流时,他们几乎都使用流利的汉语。村里人告诉我们,因为村子离小学路途遥远,孩子们多数寄宿上学,因此孩子们从小学就脱离了村庄的环境,接受统一的普通话教学,藏语逐渐淡出日常。与此同时,那些在城市求学的大学生,被视为连接村庄与外部世界的重要纽带,却也往往一年难得回家一次。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考入本地政府系统,因为在迪庆,公务员被视为最体面、最稳妥的出路。
当我们意识到这些“中介者”不会长久地留在地方时,目光重新落回那些希望发展生态旅游,但尚不熟练掌握汉语的阿叔阿姐身上,心中不免也感到一丝困境。现代性以互联网与市场经济为媒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与营生方式,却也悄然加剧了语言、身份与生态感知的位移,使得传统与当下的缠绕日益复杂。自然,不再只是神山圣湖,而逐渐被纳入资源与景观的逻辑。

与萨勇村临别当天,村里的阿叔阿姐们带着食材、工具一起烧烤,唱歌。(并清理了所有的垃圾)
人们坚信的千古不变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也如自然幻想一般,是一种文化幻象。它从来都是一个不断与周遭世界互动、更新的过程。无论是语言、仪式、还是地方知识,始终在被再造、被吸纳,也被重新理解。与其说“现代性”侵入了传统,不如说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更为复杂的、相互渗透的动态过程——一个关于文化如何在保存与转译之间寻找张力与方向的过程。如今,面对的世界图景和语言早已发生改变,曾经一以贯之的有效性也继而松动或丧失。
03 建立联结与回声的能力
生态保护需要不同专业学科和视角的交汇介入。它并非单向地灌输知识或规范,而更像是一种并肩的同行,在共同的实践中,彼此调整,彼此理解,彼此接纳。在藏族社区中,“团结”是极为重要的价值,村庄中的日常决策往往只有在所有人都达成一致后,方可实施。哪怕在我们短短一周的到访期间,也见证过两个村子的日常会议。这样的会议多由男性参加,再经由他们转告家中的女性。在萨勇村驻留的几日中,阿姐们大多羞于表达,总是在我们吃过饭后才开始用餐。在日常的聚集中,男性与女性往往也分列两侧。
一次志愿者与山水的日常讨论中,欣然让我们每个人写下对村子的疑问。我写下的是想知道当地女性的日常、生计,以及在社区中的位置;另一个则是藏语的逐渐消失对当地文化的冲击。来自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的两位女性也表达了类似的关注。因为若要发展生态旅游,承担服务与接待的,往往将是女性。她们的处境与声音,理应成为生态讨论中的一部分。这份关切也在我之后与几位阿姐的闲谈中得到回应。即使在村子尚未真正开发的状态下,她们每日的劳动几乎没有间歇。当男性在外赚钱时,日常中所有细碎却不可或缺的工作,都由她们维持着运转。

萨勇村,偶遇刚摘完猪草的阿姐们
阿姐们说,如果家中是独女或是大女儿没有出去的意愿,一般会让男方嫁入;在当地,“一妻多夫”的现象也依然存在,包括环喜马拉雅地区都有着区别于汉人的婚姻模式与家庭观。这种多元模式与藏族“家屋”的概念密不可分,在这套系统中,对屋舍的命名基于对土地的指认与命名。这种概念是在与土地的密切关系中所型塑出来的。在回程的路上,南仁村的一个阿叔就指着金沙江对岸的平坦坝子说道:“我是从四川那里嫁过来的,嫁过来才知道这和我们那边不一样。这里的男人太辛苦了,不仅要在外务工,还要回家做家务。”车上我们几位女孩笑道,城市里女性也要边在外务工边做家务,男性也是一样。
我对当地阿姐们的关注源于我长期对女性的关切共情,这种女性视角也是我加入具体环保工作的切身起点。于我而言,女性和自然在客观上拥有某种类似的结构,这种结构的类比是一种处境的共时性。即二者后天性的共享了某种处境——在制度性的关系中往往都被对象化、被规训、被剥削。但正如藏地多元的婚姻模式、也正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笔下被压迫的黑人男性。这种女性视角绝非二元论的对立,也并非是一种话语象征和策略,更不是对性别政治的功利化使用。相反,它反对一切二元对立的偏颇视阈,所关联的也远不只于“人”或“性别”的议题,而是更广义上的“共同体”的感知能力和连接方式。是去理解每一个具体存在如何在结构中被塑造、被压抑,又如何在彼此之间可能建立联结与回声的能力。
这种共同体的感知时刻涌现于村子的日常。在南仁村的一次对话中,一位村民说:“如果能发展旅游业,我们希望是让子子孙孙都能继续做下去的。” 我感动于他们和自然之间绵长而紧密的日常关系,使得他们从生命中获取了如此深刻质朴的共生理念。也更加理解和钦佩山水作为环保机构,致力于做社区工作的前瞻性。因为真正长远的生态保护,不可能脱离人——尤其是居住于此、与这片山水长久共存的社群,因为他们才是接过生态保护接力棒的真正践行者。特别是,我们无法忽视,在保护与现实的复杂张力中,并不存在非黑即白的界线。
当我们在海拔4000多米的垭口小憩时,一位村民向我们开心地展示他在这里发现的贝母,这种贝母在多年前就已经是国家二级保护植被,是濒危物种,但目前仍会被采集,以每株极高昂的价格出售至文山,并伴随着越来越难找和昂贵的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中国民间对于博物学的兴趣还在蓬勃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自然教育、生命科学、植物学的工作之中,而它带来的是我们对自然和物种的认知改变,那些为了寻找并观察高山植被远道而来的人群越来越多。如果在发展生态旅游的将来,一个向导带一个五六人的小团来看只在此才有的高山物种,同样的一株贝母不仅会带来更多的收益,也会带来物种的延续。正如曾经的盗猎者或许会是如今最好的巡护员,或许有一天,现在的采集者也将成为地方最好的博物学者。

南仁村里的老者,和暑期回来的大学生
在我们对现实的编织中,不仅需要女性主义关怀他者的视角,也需要保护他者文化的多样性。正是因为区别于现代世界同质化的主流文化,让我们看到,曾拥有过但如今却消逝的文化,让现在不再具有世界观的我们找到某种参照系,让我们能敞开心扉地面对多元存在的差异性和存在本身。
这种需要也是相互的,地方也需要外来者,以及他们带来的更多学科和科学的视角。自然和科学并不是两个并列的概念,自然是对象,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而科学则是一种方法论,是面对自然时的理解。两种概念并不属于同一范畴,更无从比较。我们可以探讨自然与社会的边界,或是两者的割裂,我们也可以讨论在传统知识和现代科学两者中,自然的不同表征。然而在根本上,我们也许应该去寻找这些概念之间的公度与连接处。
04 回归到内心
“保护环境需要先论付出,再论获得。我们藏族人似乎天然就会与他者为善,这个“他者”,可以是别人,可以是一个生命,当然更可以是无言的大自然。所有环境保护最终也要回归到人的内心。”
——肖林
在环保工作的学习和过程中,也让我看到:在现代化社会结构中被逐渐丢失的个体责任和道德伦理,以及知识与感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但藏族淳朴古老的智慧,以及每一位参与其中袒露心扉的人,都让我怀揣着希望。或许我们可以寻求到平衡的可能、更健全的机制,而不仅仅是在偏颇误解中加深对立。但首先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傲慢,承认在对待地球其它生灵时的影响与伤害,承认在发展中那些无声的牺牲者和承担者的生命轨迹。这也要求着我们,需要具体、真切地看到他者和与之缠绕的关系网络。

在南仁村的垭口可以看见萨勇村的神山
自然本不需要保护,正是因为人类对其的干预和破坏,才需要长久的修复。当再次听到远方传来低沉的轰鸣时,我不再那么悲观和沮丧。或许我们的速度还不够快,或许我们了解的还不够多,或许我们还将失去更多的生命奇迹。但我无比感激,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群在不断修复人类行动的先行者。他们无疑具有足够的耐心,宽广的视野,深刻的同理心和理解力。而他们,正越来越多。

南仁村,离别前的星空
我们离开南仁村的那天,借宿人家的奶奶站在大门口目送我们。我的奶奶曾无数次如此地目送我的离开。我没忍住地跳下车,跑过去谢谢她的招待。她布满皱纹的双手紧紧回握着我,用不熟悉的汉话说“很快回来。”
-END-
撰文/韩倩
供图/安吾农布、韩倩
排版/赵博雅
*本文来自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和引用。
如有需要请后台留言或联系contact@shanshui.org
注释:
[1]肖林,藏族,藏名昂翁此称。云南⽩⻢雪⼭国家级⾃然保护区第⼀批正式员⼯,⼀辈⼦从事⼀线保护⼯作。与⽂中此称并⾮同⼀作家。
参考阅读(上下滑动):
此称的公众号:备忘录
《深时之旅》 [英] 罗伯特·麦克法伦
《我们从未现代过》[法]布鲁诺·拉图尔
《⾯对盖娅》[法]布鲁诺·拉图尔
《⼭⽔之间》 [法] 朱利安
《汉⽔的⾝世》袁凌
《我不能在鸟兽⾝旁只是悲伤》花蚀 / 帕索卡
《守⼭》肖林 / 王蕾
《时间的旅⾏》 [澳]伊丽莎⽩·格罗兹
《末⽇松茸》 [美] 罗安清
《被牺牲的局部》马俊亚
《现代性与⼤屠杀》 [英]齐格蒙·鲍曼
《增长的极限》 [美] 梅多斯
《为动物的正义》[美] 玛莎·C·努斯鲍姆 / 玛莎·努斯鲍姆
《性别打结》 [美] 艾伦·约翰逊
《流浪猫的战争》[美] 彼得·P.马拉、 [美] 克⾥斯·桑泰拉
《雪⼭之书》 郭净